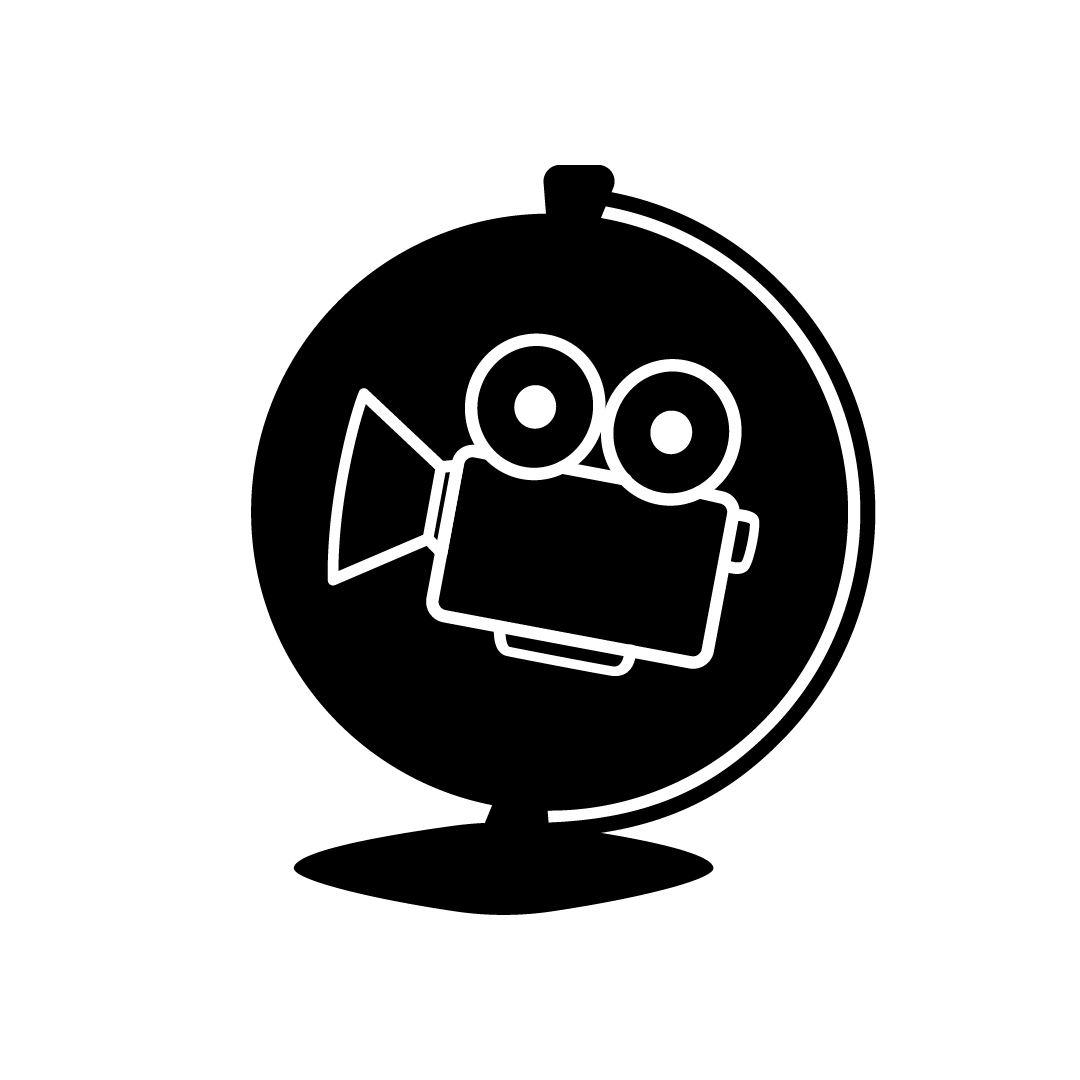像许多亚洲作家一样,我从来没有写过作为亚洲人的故事。
亚洲人与白人的相邻关系与此有关;我从来没有写过这个问题。此外,以一种不像是cosplay的方式来写移民和我的种族是很困难的。描述我成长过程中的异国饮食很容易。但要谈论为什么,例如,亚裔妇女是跨种族婚姻比例最高的人之一,但也经历了不成比例的暴力事件,这就太难了。我们被同化了,但也被过度性感和娇小,所以很容易谋杀我们,以免我们将无辜的白人男子引入歧途。
如果说有谁能在这个问题上与我产生共鸣,那就是我的妈妈,她也是亚洲人,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移民。但是,仅仅因为我们有类似的经历,并不意味着她有什么有用的意见。如果有的话,她的建议是,如果你做的每件事都完全正确,你就会很安全。我的父母从未催促我成为一名医生或律师,但要求我取得好成绩、表现完美、限制我的自由时间的压力--研究人员称之为 "剥夺权力的养育方式 "的现象--是熟悉的。
我只是在最近才审视这种想法的缺陷。也许这是因为最近才有像《变红》和《一切尽在不言中》这样的电影来说明,完美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不过,我明白了。如果我们的女儿接受这种压力,那只是为了证明我们的母亲为来到这里并生下我们而做出的牺牲。看着我在屏幕上反映出的奇特经历,使我以一种我以前无法做到的方式同情我的母亲。
变红》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有问题的迹象。许多评论都认为这部电影是关于青春期的。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在生气时变成一只大熊猫,是对月经的一种隐喻。事实上,美琳的母亲确实在电影的一个更羞辱人的场景中公开挥舞着一盒月经垫,但对我来说,《变红》的信息在于它的结局,当她的母亲在美琳的床下发现了美琳的各种违法行为的证据。钱! 流行乐队4Town! 最重要的是,学校的作业被捆绑和揉成一团。成绩是显而易见的。B+! C! " 不能接受! "我大声喊道,然后才阻止自己。
我记得我有一次在高中物理课上拿了个C,这让我立刻有了一个私人教师的课程。在我三十多岁的时候,我发现我很羡慕梅林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能把自己变成一只红色的熊猫,这让我感到很迷茫。那是不由自主的! 这不是她的错! 当她变成巨大的、毛茸茸的、可爱的、臭烘烘的时候,她并不是小的、听话的、安静的。她很吵闹,占据了空间,这很好。她的朋友们--他们接受了她的本性,而不是因为她不是什么而惩罚她--拯救了她。她可以进行试验。她的成绩不好,做出了愚蠢的决定。
像大多数高中女生一样,我属于一个小团体。我经常和他们一起玩,但我错过了很多内部笑话。直到现在,我才想到,我的朋友们在没有我的情况下花了那么多时间在一起,因为他们不像我一样有足球、钢琴、小提琴练习、实习和每个周末的家庭大聚会。结构支撑着你,但它也可以扼杀你。
" 我们发现,在旧国家拯救我们的力量在新国家是一种不便,"梅林的一个阿姨哀叹道。当她的姨妈和母亲一个接一个地放弃她们不羁的熊猫精神时,梅林选择了保留她的精神。在她毫不掩饰的个性中,她比任何一个更年长、更恭敬的女性亲属更充分地尊重她的祖先。
正如Jay Caspian Kang在他的《最孤独的美国人》一书中所写的那样,作为一个亚洲移民,我们要永远把自己的故事叠加到我们的祖国的神话上,举起《在路上》或《强尼-特里曼》这样的书,试图把这些轮廓与我们自己的生活轮廓相匹配。
这一点在《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我喜欢我的同事埃里克-雷文斯克拉夫特(Eric Ravenscraft)的评论,以及在混乱中要善待他人、互相帮助的信息。但我很清楚,这个故事--一个华裔美国妇女在寻求拯救自己和女儿的过程中经历了所有不同的生活--是一个移民父母的叙述。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母亲白天做秘书工作,同时上夜校成为一名软件工程师。这很成功!但她没有机会,例如成为一名艺术家。但她没有机会,比如说,成为一名艺术家。有一个庞大的大家庭需要支持,她不能失败。她不能选择做一个像齿轮编辑那样轻浮的事情,她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测试真空和骑自行车上。
作为一名移民妇女,意味着在你的脑海中同时拥有许多对自己的想象。不仅在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和别人如何看待我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说实话,有时我不知道你们这些人),而且在如果我们留在那里而不是来到这里,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也存在着差距。
没有人能够比杨紫琼扮演的《万物生长》中的伊芙琳更完美地体现这一点。杨紫琼在《卧虎藏龙》中优雅的运动能力使她成为我的超级明星夜空中的苍穹之一。当伊芙琳在多元宇宙中穿梭,体验到她是一个迷人的电影明星的现实时--在杨紫琼参加她的电影《疯狂的亚洲富豪》的首映式的镜头中--她回来后对她的丈夫喘息道:"我看到了没有你的生活,它很美。 "
最后,伊芙琳认识到,她所设定的标准是不可能的。她选择了自己奇特的、混乱的、人类的女儿,而不是她可能拥有的所有其他现实,这一行为救赎了他们的关系。由于相信母亲的爱,小人--她的女儿--再次成为她的女儿。这是非常感人的,没有人应该必须是完美的才能被爱。
但在观看《万物生长》时,也很难不叫出声来,但你是他妈的杨紫琼!我相信你的女儿很好,你看起来很幸福,但如果我的母亲是杨紫琼怎么办?我相信你的女儿很好,你们看起来也很幸福,但是,如果我的母亲是杨紫琼呢?我可以成为杨紫琼的女儿!选择那个现实!我可以。
与《无处不在》和《变红》更复杂的视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乌玛》,这部由Iris Shim执导、Sam Raimi制作的电影,缓慢而无聊,我无法看完(抱歉!)。看到我的女王Sandra Oh修长而灵活的脸和Fivel Stewart雕塑般的颧骨,在这样一个未经审视的代际创伤的描述中,我感到肉痛。
Umma》讲述了阿曼达的故事,她是一名韩国妇女,放弃了自己的遗产,与女儿生活在一个没有电的孤立农场。阿曼达的母亲有虐待行为,所以她逃离了。但是,当然,你不可能永远逃避你的过去。作为一个移民是如此艰难,以至于导致Umma虐待Amanda,但Amanda打破了这个循环,原谅了她的母亲,并(破坏者!)让自己的女儿去上大学。与其说是细微的差别,不如说是一个复杂的移民母女关系的模板,一分钟的版本,你可能给一个不感兴趣的白人治疗师。
但这并不重要。被同化的特权之一是,拍一部呃,不那么好的电影也没关系。我们已经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了。作为一个 "真正的 "亚洲人与一个完全美国化的亚洲人之间的冲突,或者你是否会走进一个房间,那里的人看到的是苏西-王或龙德东。还有就是你在你离开的地方可能拥有的生活,与你现在拥有的生活相比。正如韦蒙德在《无处不在》中所说,在你的脑海中持有太多的现实,你的大脑会像陶罐一样开裂。
我比梅林的母亲更接近梅林的年龄,比她女儿乔伊的年龄更接近伊夫林的年龄;我自己也有一个小女儿。我的女儿是第三代移民,而且是双亲,她将面临的冲突与我的冲突一样不同,因为我作为被同化的第二代的经历与我母亲的经历不同。
但是我确实希望能够给她至少一个礼物,除了一个不会放弃的新陈代谢(和可怕的视力)。对于她来说,我希望多元宇宙能够退去。这是我们的地方,不管其他人是否喜欢,她将能够成为她自己--红头发、毛茸茸、臭烘烘、女同性恋、功夫高手,或者是一个用热狗当手指的电影明星。亚裔美国妇女的目标是最终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无论那看起来像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