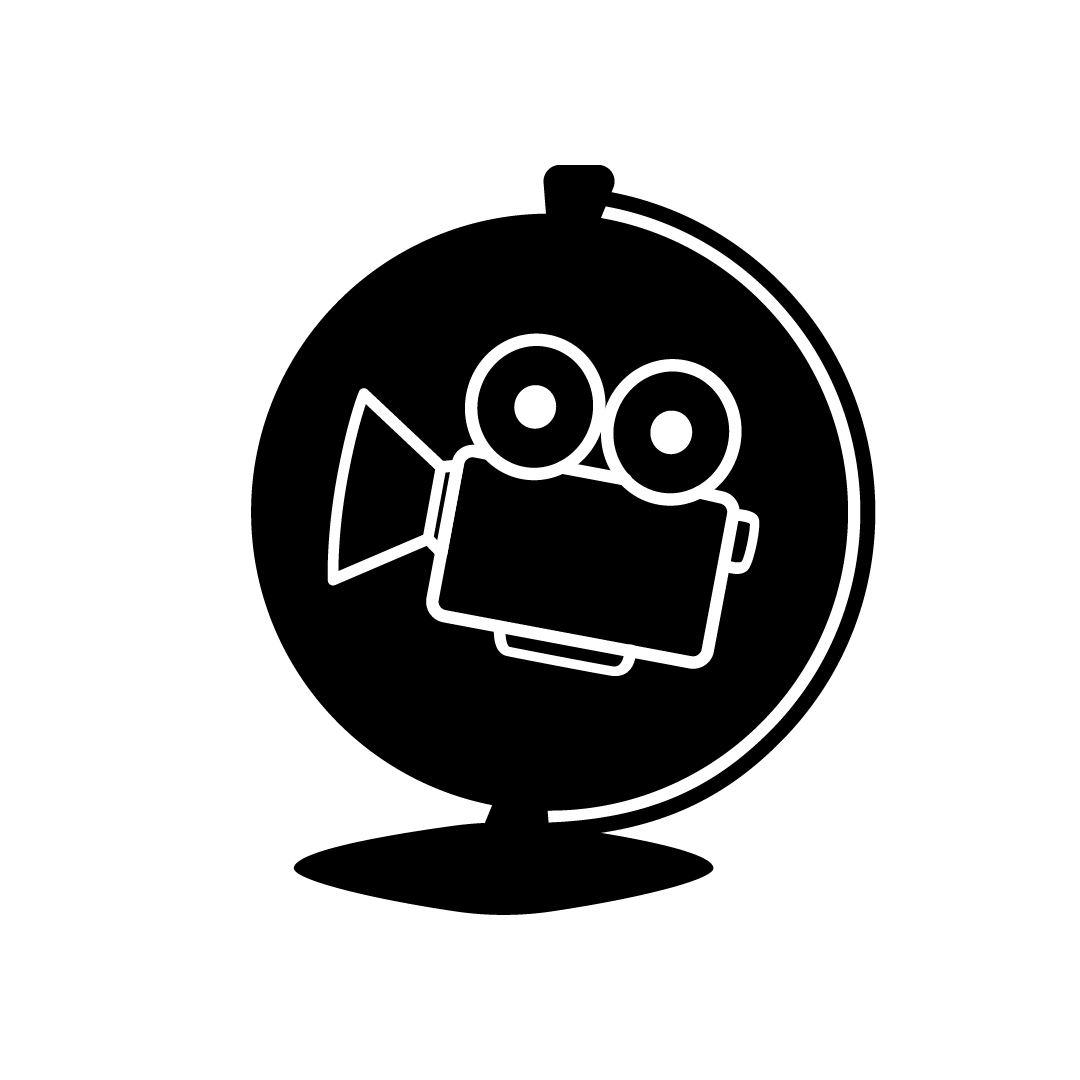在科幻电影中,几乎没有什么比世界建设更重要。这并不总是意味着宇宙飞船或遥远的星球的宏伟镜头。对于每一个像《沙丘》这样的豪华奇观,还有许多规模较小的科幻电影,其特效预算并不高或根本不存在。这些电影必须使用其他方法来充实他们的未来主义愿景。大气磅礴的配乐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营造出一种惊心动魄的气氛。巧妙的场景设计,如《原始人》中自制的时间机器或《Lapsis》中穿过树林的量子计算机电缆,可以使观众在没有尖端CGI的情况下沉浸在一个新的世界。甚至人物之间的对话方式也可以成为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定调方式。事实上,成本效益如此之高,以至于最近有一大批电影中,独特的语言模式在建立虚构的宇宙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这被称为 "悲伤的声音 "科幻片。
不是战战兢兢、泪流满面的悲伤。悲哀的意思是无精打采的,没有激情的,消沉的。一种明显的平淡情绪,有时与不自然的腔调相配。一个典型的例子。科林-法瑞尔(Colin Farrell)通过约尔戈斯-兰斯莫斯(Yorgos Lanthimos)的《龙虾》(The Lobster)时的死板表情。这部2015年的电影设定在一个幻想中的二元世界,在那里,未能与合适的浪漫对象配对的人被转化为他们选择的动物。法瑞尔的角色,大卫,在被他的长期女友抛弃后,只有一个半月的时间来寻找灵魂伴侣。紧张的! 诡异! 但他却面无表情,被动地接受了这一奇怪的命运。他平静地解释说,他想变成一只龙虾,因为除其他吸引人的品质外,它们 "一生都能生育"。 "在整部电影中,大卫遇到的其他不幸的单身汉也是以僵硬的单调语气说话,不管他们面对的是什么。兰斯莫斯的演员经常在高度情绪化的情况下保持死板,以至于这已经成为他许多电影的一个标志。在《龙虾》中,这个噱头起了作用,强调了大卫的赤裸裸的孤独感,以及他和其他人发现联系起来是多么困难。他对看似无厘头的规则的反应是冷静的,传达出这是一个个人在系统中几乎没有机会的宇宙,无论这个系统是多么荒谬。
法瑞尔已经确立了自己作为悲情科幻片之王的统治地位。除了《龙虾》之外,他最近还出演了由假名的韩裔美国电影人Kagonada执导的《After Yang》。法瑞尔扮演杰克,一个茶店老板,与可爱的企业战士凯拉(朱迪-特纳-史密斯)结婚。他们购买了一个名为Yang(Justin H. Min)的机器人来教他们的养女Mika(Malea Emma Tjandrawidjaja)了解她的中国传统,但在影片开始时,Yang出现了故障。他和这个家庭生活了多年,而米卡却被抛弃了。(Kyra, less so. " Maybe this is a good thing," she says. Cold!) 当Jake试图修复Yang时,他能够进入机器人的记忆库,但失败了。看着杨的记忆,他意识到这个宁静的机器人到底有多深的感情,他是如何有希望和梦想,甚至有爱的兴趣。它是忧郁的、冥想的、精美的镜头。它也是明显低调的。虽然杰克与凯拉争吵,说他花了多少时间来修复杨,但他们的分歧仍然奇怪地平静,好像他们会收到电击,如果他们的声音比耳语大的话。
电影中所有的对话都是这样沙哑的;人们不禁要问,在卡戈纳达对未来的设想中,是否有某种大规模处方的镇静剂在起作用。当然,这就是问题所在--悲伤的声音是推断疏远和分离的作弊代码。(另见。参见:华金-菲尼克斯(Joaquin Phoenix)在2013年《她》(Her)一开始的闷闷不乐的西奥多(Theodore),或者凯瑞-穆里根(Carey Mulligan)在2010年改编自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永不放弃》(Never Let Me Go)中讲述的平和的凯西(Kathy),这是悲伤之声科幻片的两个早期作品)。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可能会吸引导演,因为悲伤的声音有效地向观众表明他们正在观看压抑的角色。虽然《杨门女将》是一部可爱的电影,但墙与墙之间的耳语有另一个副作用。它的作用就像听觉上的新诺明,使观众对情节中最温柔的地方的情感影响感到麻木。
这就是悲伤的声音的风险。它的高度礼仪性不仅传达了一个角色与自己的疏离,它还在故事和观众之间插入了一个距离,可以抽走一部电影的情感共鸣。在另一部最近的电影《双》中,一个名叫莎拉(凯伦-吉兰)的女人在得知自己得了绝症后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克隆人。当她意外康复时,她的克隆人在法律上应该被销毁,但克隆人(也由吉兰扮演,被称为 "莎拉的替身")援引了一项法律,允许她向 "原来的 "莎拉挑战,进行决斗。更糟糕的是,莎拉的男友为了她的克隆体而抛弃了她,甚至她自己的母亲也似乎更喜欢替身的陪伴。莎拉决定,她必须通过训练来摧毁她的二重身。
这是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在理论上。然而,执行起来却让人心烦意乱。两位莎拉都是如此强烈地令人讨厌,如果观众认为如果他们简单地把事情做完并杀死对方,就不会是这样的悲剧,那就可以原谅了。作为最初的莎拉,吉兰的讲话就像她在尽力模仿一个试图假装成人类的机器人。"我为什么不哭? "她在得知自己快死了之后,死死地盯着医生,上嘴唇僵硬地问道。萨拉的克隆人稍稍有点生气,但也同样僵硬。她的声音和她的 "原型 "一样不自然,这强调了莎拉与人类的脱节程度。
与《龙虾》一样,莎拉对荒诞情况的干脆接受是为了使其更加荒诞。双》受到热烈欢迎,一些评论家将其与兰西莫斯的电影相提并论。这是对兰斯莫斯的一种侮辱。他的作品可能令人不快,甚至令人厌恶(你不可能花钱让我再看一遍《杀戮圣鹿》),但这些奇怪的东西,包括风格化的对话,都是为了一个连贯的愿景服务。而《双》的情况并非如此。脱离本身并不能使一个角色变得有趣,单单压抑也不能使一个世界变得令人信服。一个做得不好的悲伤的声音,唉,甚至可以把一个聪明的科幻剧本变成一个单调的无聊。